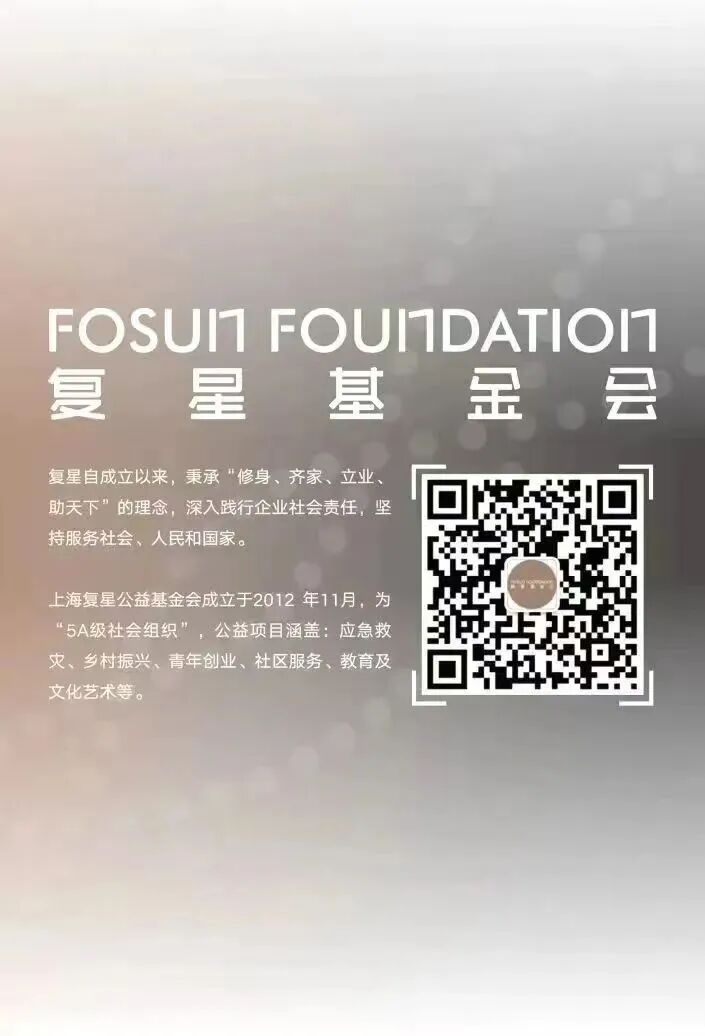世界防治疟疾日 | 缘起复星,一位清华在读博士生的加纳国田野调查

以下内容来自:复星医药
每年4月25日是世界防治疟疾日(World Malaria Day)。推动疟疾在全球范围内的可防可治,共建“无疟疾世界”,一直是复星医药持续投入的事业之一。
25日,复星医药宣布,将携手成员企业桂林南药,向安哥拉、坦桑尼亚、肯尼亚等非洲国家捐赠90万人份由桂林南药生产、通过WHO预认证(即WHO Prequalification)的疟疾预防和治疗药物,助力非洲抗击疟疾。

过去十年来,复星医药携手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下称“复星基金会”)在非洲持续开展抗疟疾药品捐赠、医生培训、社区义诊等活动,并在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中非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中进一步探索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路径,支持当地社区健康长效发展。
今年的世界防治疟疾日,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曾经在复星医药、复星基金会实习,现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就读的博士生——胡煌。让我们通过他的视野,以及他在非洲田野调查的所见所闻,走进他与复星“抗疟疾”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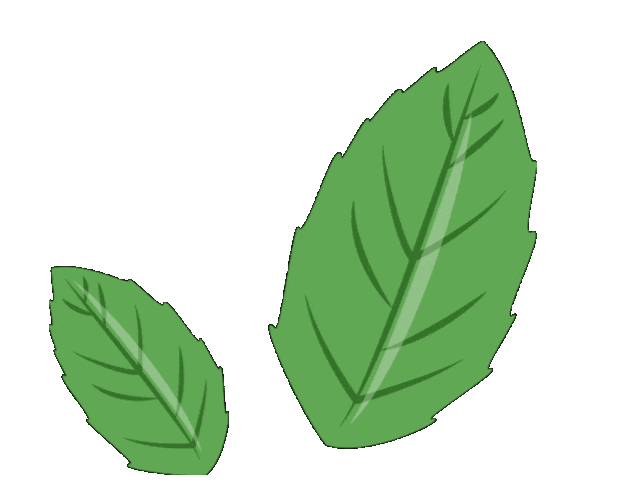
投身社会学,听见“远方的哭声”
Q
您是如何关注到“疟疾”这个研究领域的?
又是在什么机缘巧合之下来到了复星医药实习?
A
把“疟疾”作为研究方向其实是非常偶然的选择,我硕士读的是“人类学”,非常小众的一个专业,“拯救穷人生命”和“中国企业走出去”一直是我所感兴趣的两个话题。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我把选题聚焦在“健康不平等”,想去了解发展中国家在医疗健康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中国也在大力推行与南方国家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中国的医药企业能出海走到非洲的,做得最好的是复星医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产品就是“青蒿素类”抗疟药物。所以,我当时就想加入复星医药,并通过一段时间的实习,来了解中国药企出海的实际运作过程。在复星医药实习期间,对“抗疟疾”这个话题有了更多深入了解。
但是当我写完硕士论文之后,感觉“青蒿素出海”的整个故事却依旧没有写完,我想继续进行“追寻中国青蒿素出海非洲”的学术探索。自屠呦呦先生2015年拿到诺贝尔医学奖/生理学奖至今已经过去了10年,国内受众只是模糊知晓青蒿素类药物可用于治疗疟疾,但是对背后整个跨越几十年、几代人的持续“创新接力”却不熟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一直以来有关注科技与社会、全球南方、医学人文以及关怀弱势群体的传统,因此非常适合我继续完成这一智识探索目标。所以后来我选择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继续深造博士学位,完成青蒿素出海从宏观到微观跨越几十年的故事。

参加清华大学组织的校园半程马拉松完赛,“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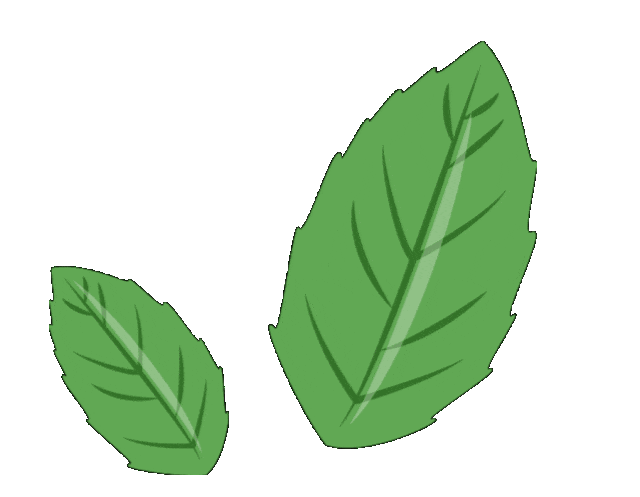
成长与实践:
赴加纳田野调查,探索公共卫生挑战
Q
在非洲田野调查的这段经历,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是否对非洲的公共卫生挑战(如疟疾防治)有了新的观察视角?
A
我去清华大学读博士之前,联系了之前复星基金会的同事,表达想要去非洲进行实地调研的意愿,因为复星医药在加纳有业务布局,同时加纳也是疟疾的“重灾区”,2023年加纳有650万人次感染疟疾,占当年全球感染疟疾人数的1.91%,超过世界卫生组织预估的500万人。这跟加纳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有很大关系,加纳南部是热带雨林气候,北部是热带草原气候,分雨季和旱季。4至9月为雨季,11至次年4月为旱季,非常适合蚊子繁衍,它们在雨季肆意生长,蚊子体内携带的恶性疟原虫一旦通过蚊虫叮咬进入人体,就会造成疟疾感染,有时甚至会造成生命危险,所以疟疾在加纳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
前往加纳进行田野调查,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生视野被打开的体验。加纳前些年经济发展迅猛,但是随后陷入困境。在加纳大学校园的酒吧里,有一位大学教授略带失望,甚至是遗憾地口吻跟我说:“如果你早些年来加纳,完全不是现在这样。”我认为这种复杂情绪和心态完全不能用学术界惯用的关于“失败国家”、“欠发达”之类的标签理解,深入共情当地人的生命体验和对现实渴望,让我真正注意到中国的创新药除了与非洲的经济往来之外,具有更广泛的双边合作的意义。由此,我也更理解复星医药的同事们身上对自己所做的事业的信念感。
在加纳的两个月我得到了复星医药在当地Tridem Pharma同事的大量帮助,跟随他们一起去分发药品,走街串巷接触各种医院、药店和其他卫生场所的过程,让我看到了超越公共卫生视角的一面。我自己在当地也有过险些“得疟疾”的经历,完整经历过一个人在出现罹患疟疾征兆到筛查再到是否用药的过程。从医药公司员工视角和当地人就医视角综合来看,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商业实践,在涉及“药品可及”、“公平分配”等问题时,应该具有微观视角去看到非洲当地人就医“实际的难”,而非“逻辑的难”。

田野调查期间与非洲儿童合影互动
Q
疟疾是非洲最致命的传染病之一,而青蒿素类药物是防治关键。你在当地观察到的这类药物是否有被广泛使用?
A
复星医药的抗疟系列产品,特别是注射用青蒿琥酯Artesun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我当时住在加纳大学里面,在跟当地一些学药、学医的同学聊天时,他们都知道这类药物,而且因为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轮岗制度,需要去医院和药厂,要去很多不同的部门去实习,所以也会接触到这类药品,虽然这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很高,但同时也面临着在一些当地小诊所使用不规范的问题。我和同事们在加纳中部城市库马西的小诊所发现有一些生产来源不明的正规药企药片被拆零售卖,原本6片装的完整疗程被切割成3片、2片分装,导致患者因剂量不足产生耐药性。我们马上采取措施,向药监局反馈其中存在的隐患。早在2016年,复星医药在阿克拉与非洲药物安全警戒协作中心签署了药品安全性监测战略合作协议,这个以非洲地区为重点关注区域的药品上市后安全性监测项目,为药品在非洲地区的安全使用提供一线数据支持。也从药品质量监控上保证了青蒿素联合疗法药品的药物疗效。

与Tridem Pharma加纳同事共事
Q
复星医药一直深耕非洲,目前科特迪瓦园区正在建设中,未来将实现药品的本地化生产、配送及销售,在您看来,跨国药企的本地化生产对于非洲当地来说有什么积极意义?
A
中国人有一句古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认为,复星医药科特迪瓦园区建设项目是中非医疗合作的重要实践,最直接的是提升整个西非区域相应药品可及性。非洲长期依赖进口药品,供应不稳定,前些年受全球疫情影响航运阻断,多年来因疟疾而死亡的人数出现反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远洋航运阻断导致部分抗疟药品及其他物资供应中断。复星医药科特迪瓦园区未来建成后,可以直接进行抗疟疾药物的本地化生产,增强了非洲本地制药的韧性。这是许多跨国药企在中国曾经实践过的方案,在我看来,复星医药也在践行这一全球化的路径。科特迪瓦跟其他南方国家一样,缺乏专业化人才。复星医药在科特迪瓦园区设立GMP实训基地,能帮助培训当地技术人员,创造就业,增加当地收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还有外汇的问题,非洲国家每年因药品进口消耗大量外汇,本土化生产可减少对外依赖。非洲绝大多数国家在传染病防控上依赖外部资源,疟疾是非洲最致命的传染病之一,撒哈拉以南地区占全球疟疾死亡病例的95%以上。在科特迪瓦进行本地化生产可快速响应需求,缩短供应链,降低药品价格,使更多患者获得治疗。本土化生产还能使非洲在突发紧急情况时快速采取行动,不仅解决了非洲药品短缺的燃眉之急,更通过技术转移、产业升级和人才培养,为非洲构建自主的医药工业体系奠定基础。尤其在传染病防控方面,本地化生产缩短了药品供应链,降低治疗成本,能够显著提升非洲应对疟疾等疾病的能力。
Q
在疟疾防治领域,在非洲知名度最高的是一家中国企业,而非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大药企,您认为主要原因有哪些?
A
首先是得益于中国的科学家早期在探索青蒿素药品创新发明上走在世界前列,才让之后的企业得以拥有一款世界领先的创新药。其次是国际视野,我也注意到中国药企在近几十年来进行的多种形式的对外合作模式出海,而这其中,复星医药是为数不多真正把WHO-PQ这条路走通,并且持续投入在开拓国际市场的企业,从这一点看我认为复星医药是一家具有“熊彼特创新精神”的企业。复星医药自主研发的注射用青蒿琥酯已经累计在非洲救治了超过8000万重症疟疾患者,并且青蒿素系列产品也成为了“WHO推荐用药”,这跟一般药品的商业化是有所区别的路径,涉及大量公共卫生议题,背后牵涉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科学家、公共卫生专家等多方主体,企业需要捋顺他们相互之间的关联,形成合作共识,是一项艰难但值得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其他欧美跨国药企在疟疾这一领域选择不再加大投入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复星医药的产品已经做到了超高的市场份额,且产品品质高,其他的企业再投入已经进场太晚了。

走访加纳首都阿克拉市一家药店,了解注射用青蒿琥酯在当地的使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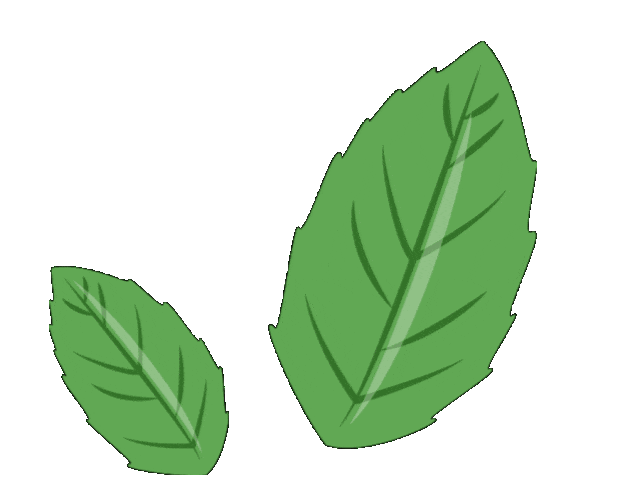
与“理想”对谈,关于未来的展望
Q
结合您的学术研究和实地实践经验,您认为医药企业未来在非洲疟疾防治中还可以探索哪些创新模式?
A
去年九月份的中非合作论坛上,我们国家领导人提出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在疟疾方面,中方提出愿同非方成立中非医院联盟,共建联合医学中心。向非洲派遣2000名医疗队员,实施20个医疗卫生和抗疟项目,推动中国企业投资药品生产,继续对非洲遭遇的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建设,提升非洲各国公共卫生能力。
这是非常强烈的合作信号,未来的全球抗疟疾事业,可以考虑跟中国政府牵头且具有全球抱负的项目进行合作。利用自身的产品优势,既能满足非洲当地社区需求,又能提升中资企业的社会责任。
Q
您作为曾深入非洲的年轻学者,您觉得一家怎样的企业能吸引全球人才的加入?
A
我非常认同一位曾经接受我访谈的药企负责人的说法,吸引人才最重要的是让其他人看到这是一家“有理想”的企业。有理想体现为企业的投资决策除了考量短期收益,还会大量长期布局未来。愿意在其他企业不敢尝试的领域去探索试错,进行熊彼特创新式的“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种敢于冒险的精神,是会吸引到具备“流动性期望”的全球人才的。
Q
我们读到您在一篇文章结尾写道“我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明,一定不是建立在传染病对人口增长产生“自然抑制”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悲观预言之上”,特别受到触动。请问您能跟我们更多的谈谈背后的想法和感受吗?
A
这一想法主要来自我跟其他人聊我的研究时的遭遇。一开始别人听完的反应都是噢噢,你这个研究很有意思。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大部分人心里可能都在犯嘀咕为什么要关注“远方的哭声”?那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一点尤其让我意识到中国人在经历快速的社会转型变迁过程中,心灵很少会被跟自己没有实用性关联的事情分散注意力,因此对远在非洲的疟疾患者能不能及时得到救助并不太关心,也很难关心得上,最终他们遇到的困难会被笼统表述为“发展”问题,似乎经济没有发展到中国这样的程度就意味着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没有一揽子解决方案,投入公共卫生是避重就轻。
我恰恰想说的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从乐观主义视角我们看到的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全体人类福祉改善,人类新生儿死亡率下降,致命传染病得到控制,新的技术被应用到日常生活之中。但是有一点往往被技术进步遮蔽,那就是人类的集体道德也在同步提升,曾经因物质匮乏导致出现病痛无药可救的问题还只是小问题,但现在整体社会的物质得到极大丰富,全球连接愈发频繁,人类还有什么理由拖延去解决那些危及生命的人道主义难题呢?在这个问题上,复星医药的同事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她说投身医药行业,比起赚钱,其实自己更关心的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关心的公共卫生问题的伦理层面,也是想试着跟她进行对话,我们在校园里、书桌前做的学术研究,也有一样的让世界变得更好的目标。